走进乡愁(原创)
闫会作
阔别近四十年后,再悠然漫步在故乡的田间小路时,那种眼前的陌生和遥远的熟悉,在我的心底纠结成无限的感慨,一再泛起的是直把故乡作他乡的错觉。好在父亲用他八十年的人生阅历,帮我翻开家乡这尘封已久的画卷,一页页领略过往的沧桑,仔细品味缠绵而醇厚的乡愁。
三十多年的戍边岁月,让我熟悉了大漠苍凉、雪山冷峻、边塞孤寂,看惯了月圆月缺、雁南雁北,吃惯了烤肉、抓饭和馕饼子,却让我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家乡,在不断加深的乡愁中模糊了故乡的记忆。我已熟悉了边关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却生疏了故乡的一硷一畔、一村一庄;习惯了“胡天八月即飞雪”、铁马冰河、边关冷月,却生疏了关中杨柳桃花艳、渭城朝雨、秦川黄土。我那由油泼辣子腰带面垫底的肠胃,早已充满了奶茶和牛羊肉的腥膻。我虽曾无数次梦里漫游故乡,却没料想真正踏上故土,早已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唐•窦叔向《夏夜宿表兄话旧》)我和眼前的乡亲、村落、阡陌、小河,相互都显得如此的生疏。
我得从头走进故乡。
好在有父亲带着,便不会走弯路。父亲的八十个春秋,寸步未离地在这块土地上守望耕耘,生儿育女,背着日头渡时光。虽然从未涉足过更大的世界,但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落下了斑斓的时代印迹。新旧中国两种反差如天壤之别的社会,单干、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改革开放那万花筒般的缤纷时代,穷日子、苦日子、安闲日子那饱含着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激荡着故乡的变迁,也让他平平常常的人生,积攒了足能说满后半生的故事。这故事就是家乡历史,是引我走进乡愁的向导。
父亲用他缓慢的步伐和娓娓的叙述,带我缓缓走进曾经久久萦回于梦中,如今却异常陌生的家乡。我曾经赤脚嬉戏的黄土小路,如今已被水泥覆盖,在秋田和村落间蜿蜒。父亲的话语也如这小路自然婉转,既随意零散好像没有逻辑,又显得自然有序而顺畅连贯。眼前看到的景、随机碰见的人、张口聊到的事,都能转承自如地娓娓说来。走到村里一条绿荫盎然的沟边,他说,这是过去的城壕。解放前为了防土匪,打城墙取土挖出来的。我小时候爬上爬下的高大的土城墙,已经了无痕迹,村子已经越过了城墙向四周扩延,草树长满的城壕已经成为村子中的一条绿色环带。看到房前屋后挂满柿子的柿子树,他说,旧社会穷人家怕的是“两红一黑”。“两红”就是柿子和辣子,“一黑”是皂角。这些东西熟了,就是漫长的冬天和青黄不接的二三月,缺衣少粮的日子,谁不怕!如今不仅不怕了,柿子一红倒成了秋天的景致了。看到村头几孔坍塌的窑洞,他说,你还记得吗?这是过去的小学校。你就是照着煤油灯,从这里开始读书的。你这一辈子能到外面干事,这窑洞是有恩的。这是我的小学。几孔窑洞,一圈土墙。一孔窑洞里,两排土坯砌成的台子,分属两个班级。一个班面朝里,面朝外是另一个班,老师给一个班讲完课,布置好作业,走到另一头接着给另一个班上课。这窑洞便是我人生的起跑线,而顶着一柱黑烟的煤油灯昏黄的光芒,照亮了我人之初的起点。我那缺少纸张、缺少课本、缺少课桌板凳的小学时光,恍惚如昨。我注目着这残破废弃的窑洞,仿佛仍有丝丝灯光和朗朗童声传出。走到河边的桥上,他会说,你上学那会儿还没有桥,春夏秋冬都是跨“列石”(在河里等间隔垒的露出水面的石头堆)过河。如今学校的条件好得很。娃娃们上学有车接车送,不用赤脚过水。学校全都是楼房,玻璃门窗,还有暖气,不缺书本,不缺纸张,不缺笔墨,啥都不缺了。我那曾经什么都缺的学校,如今已是一片白墙橙顶的楼房,在绿意盎然的田野中格外的显眼。
而不时“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招呼,更让我如同身在异乡,我从父亲与乡亲们家长里短的话语,以及由此牵连出来的旧事遗闻中,慢慢地对多年“蝴蝶梦里家万里”(韦应物诗句)的家乡,越来越亲近。碰见同村的人,父亲给我讲排行、算年龄、论辈分。直到人都走远了,还在说这人家庭怎样、老人如何、孩子多大、如今日子过的多么的好等等。碰上别村的,也要给我说,这人姓啥行几、那门那族,与别的家族关系如何,曾经因何人何事与那一家族结下过梁子,后来又如何化解,和好如初,现在这族人家由谁在主事等等。咱们这里就是这样,遇到矛盾问题、有了事情纠纷,先得找主事的说话。不然的话,啥事都办不成。如此等等,方圆三五里的村子,父亲不仅都有熟悉的人家,而且对很多人复杂的家庭、社会、宗族、亲戚关系也都清清楚楚。看似父亲是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一个又一个遇到的人,实际上是借着熟悉遇到的每一个人,让我去熟悉了一个家族、一个村子,进而熟悉了家乡。这种浓厚而亲近的乡情,让我感到,比起看似规整繁花、热闹拥挤,却人情冷漠、邻里对门互不相识的城市,农村看似零乱无序的表象下,却以古老而深厚浓郁的宗亲乡情,凝聚成更加坚实牢固的稳定力,乡里乡亲,古道热肠,纯朴友善,处处因为有情而显得格外有序。
人的亲善渐渐唤醒了对生养我的这方水土的亲切,虽然它较我看惯了的森林草原、戈壁大漠,显得拥挤而逼仄,条块窄小,层层叠叠,纵横交错。但却有着贯通血脉、激活脑海最深处记忆的魔力。父亲对他的土地熟悉到如数家珍,而他对每一块地、一道沟、一条渠、一片林的介绍,都能使我想起在这片黄土地里光着脚撒欢成长的点点滴滴。他会不由自主地评说路边的庄稼,遇到长势好的,就赞说这家人勤快,经管得精心;碰到长势不好的,就说人家偷懒哄地。土地最实在,从不亏人。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季。看见在地做活的人,他会上前去聊聊庄稼的长势、说说浇水、施肥、除草和收成、粮价等等。看着在地里忙活的都是些上了年级的人,他会由衷地担忧,以后这地谁来种呢?我劝他不用担心,以后科技发达了,很少的人就能种很多的地。他说,再少也得有人干,现在地里看不到年轻人了。都不种地了,将来吃风拉屁呀。大半辈子艰辛、沧桑和短缺生活的岁月,让他始终坚信手里有地、仓里有粮,才是踏实而安稳的日子。他们一辈接一辈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和着泪水洒血流汗的耕作,才使得脚下这些土地变成今天这般的肥沃丰腴,才有了雄厚绵长的地力生长出赖以生存的粮食,也生长着一茬又一茬希望,才使一个又一个村庄有了祥和、安静、自足、美满的景象。他希望年轻一辈能珍惜这一切,精心侍弄土地。看来年龄也能酿造出乡愁。
父亲的叙述帮我连接着记忆中的故乡,带着我从边关走回家乡,用亲近消解着距离制造的乡愁,用实景缓释着岁月发酵的乡愁。可当我感到父亲言语和思绪中隐隐流露出由年龄酿成的乡愁意味时,我突然感到,我这距离和时间酿制的乡愁,还能走回来,而父亲那由年龄、时代差异滋养出来的乡愁,怕是很难走回去了。八十岁老人的步子总是慢悠悠的,不仅是腿脚不便的缘故,也因为那些纷繁的往事、漫长的过往、太多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莫名忧虑,随时都能投射到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上,疯长出瞬息万变、永不枯竭的话题。父亲说不完的话,看似帮我熟悉家乡,又何尝不是倾诉对在外儿女长期积攒的思念呢?又何尝不是我的乡愁的反照呢?看着父亲艰难而蹒跚的步子,我很难把眼前的父亲与年轻时扛着一口袋粮食上楼如履平地的父亲,甩起梢头系着红缨子的长鞭子赶着四挂马车威风凛凛的父亲,放下铁锹拿锄头水里来泥里去风风火火的父亲联系起来。是什么让一个曾经精力充沛的身躯,变得如此地弱不禁风?不由得嗟叹,岁月到底是温情脉脉,还是冷酷无情?岁月的多情是能让生命平等、自然且顽强地繁衍生息,岁月的无情,是它不动声色、一视同仁地让所有的生命走向衰老和死亡,而岁月的神奇是于无形之中,将父亲的精神和气力转换成脚下这块土地生息不竭的力量。
黄昏的霞光在日渐成熟的秋田里,泛起层层波光,我望着房子越盖越高越好看的村庄,等待着记忆中最温馨情景,袅袅升腾的炊烟,缭绕于宁静祥和的村庄上空,四处弥漫着家常饭菜的香味。可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看到炊烟升起。父亲说,现在都用气、用电做饭了,没有烟了。我有点失望,可口舌中泛起的仍然是妈妈的手擀面、酵面发的蒸馍、玉米面发羔的味道,脑海里仍然是风箱抽动的吧嗒声和柴火映红灶堂的画面。这味道、声音、画面,已经成为渗入骨髓的记忆。尽管我走遍了天南地北,也品尝过各地的特色小吃和珍馐佳肴,但总也忘不了家里的粗茶淡饭的味道。
沉浸于乡愁之中,是一种滋味醇厚的阅读。父亲用他八十年的阅历,让我真切地看到了,历史是怎样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中更替,家国又如何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中兴旺。而我这近乎偏僻且普通的家乡,同样是一卷立体多维、浓墨重彩的乡村的风情画卷。在这里体味到的人情世故、伦理纲常、门第宗族、血脉传承、风俗习惯,同样是在阅读乡村的历史与现实。看似简单悠然,琐碎凡杂,实则厚重纷繁。那怕是再简单的人生,突然注入八十年的阅历,不仅会给我的人生增加了厚重的色彩,也会打通我了解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任督二脉,让我知道走过的路有多么的曲折崎岖,前辈们前行的每一步是多么的顽强而坚忍,更能让我清楚,自己的根在那里、昨天怎么样,今天又是从何而来,将来要怎么走。老辈的勤奋节俭、任劳任怨和埋头苦干,积攒出了今天的丰富、繁荣和发展。未来会怎么样,就得靠我们自己去奋斗了。
漫步在故乡秋天生机勃勃的田野上,陶醉于累累果实浓郁的香甜之中,浸润在过往岁月和悠长的人情世故中,慢慢地有了依偎在妈妈怀抱的感觉。这使我明白了,落叶归根是乡愁赋予游子无穷的动力。从来没有力量能消解乡愁的缠绕,因而自古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挡住游子回乡的步伐,
溶溶月色,淡淡轻风,享受着故乡的明月,我又想起了边关的苍茫月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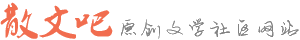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