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炎炎的夏,仿佛只剩下了莲的清凉,不记得从何时起,喜欢上张望着窗前的那片荷塘,因为在老家门前,也有一大片荷塘,每年的盛夏,都是这般清幽,这般宁静,这般的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翠作裳。
老家,依旧坐落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静静地蜷缩在离家2355英里的公寓中,细细的品一口麝香猫的醇香,细细回味着儿时故乡的那棵桃树,妩媚桃花,现今早已俏满枝头了吧,那时的我,最喜欢默默的站在书棹旁,手捧一叶桃花,看的出神,仿佛自己便成了祖父手下的那只半旧的狼毫,浓墨泼洒,细笔勾勒出桃花的喧闹与芬芳。
少年不识愁滋味,却总喜欢故作多愁善感,纳兰词更是爱不释手,颂读的淋漓尽致,口灿生花,不知却从未真正的靠近过这个镜花水月般得男子半步,长大后渐渐才明白,原来,在这个男子的心中,只有记绣塌闲事,并吹红雨的那个女子,和那片魂牵梦萦的故土吧。年少时时常翻阅的那半卷纳兰词的手稿,如今还是一样的被祖父视作珍宝的的供在书橱里吧,早已不记得什么时候打开过那扇橱门了,现如今的书桌上堆满了的,都是些市场营销,管理学,商务会计的书籍,却不知老家中的那几本字帖,那几册宋词,是否早已粘满了微尘,亦不知道,那些弟弟妹妹们,是否正捧着唐诗宋词,寸断愁肠,感叹岁月催人老呢。
手指轻轻的叩打着半新的立体书桌,浑浑噩噩的呆在这所谓的异国他乡快有两年光景了,依旧觉得,自己还是融入不了这般的世界,小桥伊人,烟雨红尘,早已被这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所替代,耳边的丝竹古琴,则变成了传世永恒的爱的罗曼史,眼边的柳体,早已换成了标准印刷体,连那浓浓一得阁的墨香,都已换成了而今喷墨那股说不清的味道,A4边脚留下的那点残墨,静静地躺在那盆文竹旁,一动不动,文竹,是从老家带来的,上飞机时还是快要干枯了的,如今却养的枝繁叶茂,怎么,你更习惯这边的水和土?自嘲的笑了笑,登机口,没想到会哭,也想不到会哭,父亲看着落了半个钟头眼泪的我,淡淡一句,走吧,便把我送上了飞机,祖父执意不肯来送我,推脱说,年纪大了,不可到处走动了,父辈们都没有点破,祖父是最疼他的长孙的,又怎会不想来送呢,只是祖父早已不再是扛得起分离之痛的年纪了,也不想再经历这些离别之苦了吧,就这么的,一只十四寸的登机箱,拖着满箱的思念与回忆,走过了安检,走过了登机口,走过了,整整两年。
早些天收拾衣物时,发现了放置在衣橱角落保存的完好如初的那半包乡土,还有半包,则养在了那盆文竹里,父亲说这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我想想,这更多的也就心里作用吧。手中的咖啡凉了,在这个国度,凉与不凉是没多大的差别,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咖啡那股醇厚的香味,以前这个点,早已和祖父两个人晃晃悠悠的去集市喝下午茶了,一笼烧卖,一笼汤包,在加上店家一壶清新的碧螺春,滋滋润润的又度完一天,两年前,开始慢慢接受咖啡,红酒,红烛,刀叉,如今才知,所谓的接受,也不过是熟悉罢了,哪又会谈的上喜好与享受呢,心里惦记的,还是那半笼油而不腻的点心,和那半盏残茶吧。
而今,独剩下手中的咖啡和身旁的那把椅子了,心里时常默默的念叨着,为了那只狼毫也好,为了那半壶碧螺春也好,总该回家一趟了吧,略翻了两三页刚刚写完的《这一年,二十一二岁的花季》,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写写画画了,是饱尝心酸之后?还是与至亲们天各一方的时候。老家的童年,是在泥泞的田埂上度过的,拖着一本全宋词东摇西晃,屁颠屁颠的跟着祖父去放牛,老牛饮水,都是那般的一丝不苟,细吞慢咽,有时,祖父会将我高高的举起,跨坐在牛背上,任凭老牛独自觅食,自己却拿着那本残旧不堪的李后主词集和他的小茶壶倚在了树荫下,炎炎的夏日,昏昏沉沉,似乎连驱日人都接受不了这份酷热,前驱后赶,风尘仆仆,这一赶,便赶了二十年,而今,生活的世界,似乎只剩下了夏,制冷机代替了那柄扇了二十年的蒲扇,就这么的,渐渐的习惯了夏,习惯了夏的生活,习惯了那些两年后依旧觉得陌生的东西,该回家了吧,习惯,永远不会代替喜欢,回家吧,那或许只有五钟头的距离,回家吧,再去见见那熟悉的人,看看那熟悉的景,回一趟吧,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每个出门在外的游客,都在忐忑着曲终人散,物是人非。每个客居异乡的游子,又何尝不想轻轻叩响那扇朝思暮想的家门,轻轻说一声,妈,我回来了。每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儿女们,又何必非等到落暮黄昏之际,才匆匆回望一眼,决定落叶归根呢,回吧回吧,趁着青春还在,家还离我们不是太远,回一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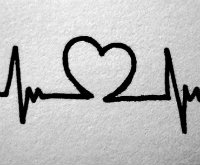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