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故事
记得童年时,一到冬天,我们就会围坐在生产队的喂牛屋里,听老人讲些乌七八糟的故事,在我们那里叫“瞎话”,意思说这些话都是假的,你听听乐一乐就可以了,不要信以为真。
每到冬季寒冷的季节,窗外的风不时地呼啸着,撕裂着,仿佛在寻找着每一丝空隙钻进屋里。小时候家里比较穷,房子都是用石块垒的墙,屋里也是简单地用泥巴糊一下,一到冬天凛冽的北风就会从泥巴的裂缝立挤进来,使本来就寒冷的屋子更加寒冷了。
那时总感到冬天特别冷,也特别漫长,天常常是灰蒙蒙的,寒冷的北风几乎天天都在刮,冷得让你发抖打颤,仿佛使人掉进冰窟窿了一样。一向受弱单薄的我总是卷缩着脖子,浑身瑟瑟发抖,母亲看到后总是赶忙从院子里抱来一些秸秆,点燃让我烤一烤,在火光点燃的那一瞬间,我即刻感到了融融的暖意,只是这种温暖是短暂的,灰烬之后又一片清冷。于是我渴望有一个暖和的去处。
村西头有一栋老房,年岁已久,房顶上缮的草都已塌陷,院落比较宽敞,当时是生产队的队部和养牛的地方,有几个年龄和辈分稍长一点老人是负责喂牛者,其中一个牛屋的老人姓张,大家都喊他张老头,论本分我应该叫他爷,有六十多岁,一张晒黑的、饱经风霜的脸,光头上冬天经常戴一顶黑色的破棉帽,动作总是慢慢腾腾的,微弓着背,一幅慈祥和善的样子。也许是禁不住长夜的寒冷和寂寞吧,每到傍晚,老人便早早在屋子中间升起一堆火,并不时还添些木柴、秸秆之类,火堆的上方还搭着一个架,正好挂着一只被火烧得漆黑漆黑大水壶。火势熊熊,偌大的一间屋子很快变得暖和起来,这里也成了我躲避寒冷的一处乐园。因为它让我感受到那份实实在在的温暖和惬意。
吃罢晚饭和我一样心情和目的的乡邻们便陆陆续续涌进这个牛屋,既为取暖,又为打发这漫长的寒夜。随手扯些干草,大家便围坐在火堆旁,素日冷清的牛屋顿时热闹起来,东家长西家短的闲扯一番过后,一些出过远门见过世面的人,便会讲些异地的风俗伦理以及道听途说的奇闻怪事,不管是真是假却也听得大人小孩津津有味。火在老人的拨弄下越燃越旺,直烤得每个人的脸都是通红通红的,火上的水壶也发出嘶嘶的响声,夜深了我和着昏黄的灯光,看着每个人的脸上没有一丝倦意,有的实在困了就躺在干净清洁的麦草秆上打个盹,起来揉揉眼睛再听那些老人讲些民间的传说或者聊斋之类的故事,这其中就数张大爷讲鬼故事讲得最好,他的肚子里似乎蕴藏着无尽的鬼故事,只见他把烟袋的烟灰轻轻磕掉,再装上烟末,然后就着火苗猛吸两口,一股呛人的烟未随之弥漫在整个牛屋,于是许多妙趣横生的鬼故事便在烟雾缭绕中一个个上场了。什么鬼妻、鬼火、鬼打墙等等,总是听的人毛骨悚然,目瞪口呆,有时我听得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了,总是捱到有大人回家时才敢和他们一块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黑乎乎的夜,总感到到处都有鬼怪躲在黑暗里,瞪着阴森森的眼睛在看我,我总是紧紧地依偎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地回到家里。
张大爷讲的鬼故事我记得最清的就是,“说两个汉子比胆大”:一个汉子好吹,一个汉子不好吹,但谁也不服谁,好吹的汉子说:“我敢到咱村乱坟岗里和死人一起睡觉”,不好吹的汉子说:“好!有胆量咱们打个赌”,“打啥赌?”“咱村刚刚饿死一个人,正躺在乱坟岗里,你敢不敢去喂他吃饭?”“那咋不敢,我敢!”时值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北风呼呼的刮着,好吹的汉子端着小米饭,大步流星的走进了乱坟岗,乱坟岗里一片寂静,阴深深的十分恐怖,远处还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哀叫声,使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吹的汉子撞着胆子走到死尸旁,蹲下身去颤颤惊惊得用小勺往死尸嘴里喂饭,他喂一勺,死尸吧嗒吧嗒竟咽下去了,他心里感到惊奇,是不是自己眼睛看错了,他又喂了一勺,死尸又咽下去了,这时好吹胆子大的汉子,心里开始发怵,不听使唤的手,开始喂得越来越快,恨不得一下子喂完,但是他喂得快,死尸吃得快,这可吓坏了好吹的汉子,把碗向死尸脸上一扣,嘴里说着“我让你吃”,不顾一切拔腿就跑,这时躺在地下的死尸,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一边追一边喊:“别跑,别跑是我呀老弟”,他越喊那老客跑得越快,一口气跑到家里,一头栽倒床上一病不起。其实他喂饭的死尸,是不好吹的汉子,早早到乱坟岗,把死尸拉到一边自己躺到哪里装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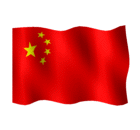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