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向南疆行
再向南疆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次南疆之行,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二十七年前我曾作为一名战士,坐着七天七夜的铁皮闷罐火车和三天三夜的解放汽车,来到云南中越边境参加那场刻骨铭心的战斗。今日,我作为一名旅游者,坐着厦门航空公司四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广西中越边境参加一次和平、快乐之旅。时空的变迁,岁月的追忆,不能不让人感慨唏嘘。
历史的见证——友谊关
友谊关是我们参观的第一站。据介绍这是一座始设于汉朝的雄关,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沿用过鸡陵关、大南关、南关、界首关等名称,镇南关之名始于明代,1953年1月改名为睦南关,1965年1月更名为友谊关,是陈毅元帅的亲笔题词。
友谊关,在我曾经年轻的军旅记忆中,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眼望着这座古朴、雄伟、庄严的关楼和周围苍翠蜿蜒的群山,我不时涌动着一股澎湃的心潮。友谊关那宽阔广场上喷射的水柱有十几米高,四周落下的水雾漂向游客幸福的脸上,花坛里姹紫嫣红的花儿在秋日里烂漫地开放着,这里的环境是如此的宁静、祥和。不过稍加留意,你还能发现广场左前方不远处用迷彩色伪装着的越南哨所,仿佛在暗中注视着边关通道上的每一个行人,同时也不难发现右前方高山上依稀可见的中方哨所,仿佛也在俯瞰着对方的一草一木。这二个哨所,在时刻提醒着我们:这里是中越边关,不能越雷池半步。
友谊关,你见证着中越两国人民共同抵抗外国列强侵略的战争历史,特别是在友谊关二楼的会客室里,谱写着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与越南胡志明主席建立起来的一曲同志加战友的赞歌。同时,友谊关,你也在低低泣诉着中越两国在国际大气候风云变幻中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
和平的呼唤——小集市
这次旅游我不得不说一说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硕龙镇,那里有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德天跨国大瀑布。从落差50米的山崖上飞流直下的瀑布,落在岩石上,到处飞扬着水花,水花的尽头是一片迷雾茫茫,远看就象一幅巨大的银幕,展现在游客的眼前;坐着越南人伐的小小竹排近距离站在瀑布下,倾听来自天籁之声,仿佛使人想起白居易《瑟琶行》中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中的美妙意境,不得不使人仰叹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景区里还有中越835号界碑,界碑旁并立着唯一的一块刻有汉字的面向着越南的清朝界碑。这斑驳陆离的界碑,仿佛诉说有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历史故事。界碑的一边是建在边界通道上一侧长约四、五百米的的一条中方步行街,可以算得上整齐清爽;另一边则是越南的简陋小集市,面积不过三、四百平米,地方凹凸不平,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块小荒地上用木板搭起的货台,进行简单的买卖交易。内地的游客无法想象在这里可以不用身份证和出入签证,一脚踏上越南的国土,与越南边境居民进行近距离接触,在集市里可以讨价还价,买些越南土特产,例如:越南的咖啡、香烟、香水、菠萝蜜干、花梨木筷、舒筋活血天草油、白虎膏等小百货和工艺品。也可以用十元人民币兑换上二万多元的越南币,成为快速致富的“百万元户”。
小镇里有一条清澈透明的的归春河,它的源头在中国,迂回曲折流过越南,把中越两国紧密地连在一起,最后回归到祖国的左江。这条河也很自然成了中越两国的界河。据导游介绍,中国边民绝少往越南跑的,倒是有不少越南妹子,趁着傍晚时分或美丽的月色,划着小小竹排悄悄过河来,与镇上的情哥哥约会对歌,然而带着嫁妆结婚。当然,结婚证是不要的,因为极大部分是非法的。
在这里,也许语言是无国界的,贸易是无国界的,爱情是无国界的,和平更是无国界的。
生命的探秘——长寿村
不论是王候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每个人都有想往和追求着自身的健康与长寿的权利和执着。古有秦始皇派五百童男五百童女东渡扶桑寻找长生不老药,唐代有高僧玄奘历尽千辛万苦到印度求取使人长寿的真经,历史上更有不少奇人术士独居深山野岭,炼制所谓的长生不老药。今天的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就更为强烈。追求绿色能源成为一种创新,追求健身运动成为一种时尚,追求绿色食品成为一种保健。
我们按照长寿村的村规习俗,怀攥着三个小红包(内装着一至十元钱,每人一个),怀着虔诚和探秘的心去拜访了巴马县长寿村的三位百岁老人。据有关资料介绍,如今已是113岁的黄卜新老人,早年参加了韦拔群的队伍, 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右江革命处于低潮时,由于与部队失去联系,回到老家种田过日子。在家中,遭遇到丧失二子的不幸打击。面对命运的不公,黄卜新以博大的爱心和乐观主义精神,帮助另一个残疾儿子娶妻成家,把从小失去父亲的几个孙子培养成人。据老人的家人介绍,黄卜新老人到了八九十岁,还能种田犁地,年纪过百仍能看牛放羊。如今113岁了,他仍然脸色红润,耳聪目明,笑声爽朗,不断与每位游客亲切握手交谈,一遍又一遍地给每一拜访者摸头、拍背、施福。
另外,我们还拜访了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百岁老姐妹。还未见面,我们就看到一位老人听到楼下晚辈的叫喊, “咚、咚、咚”下楼。下楼的正是姐姐黄妈干,今年106岁,小的叫黄妈学,今年103岁,她们的故事更被当地村民传为一段佳话。巴马是百色起义的发源地,黄妈干和丈夫是一对革命的夫妻。由于长期的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和浴血奋战的恶劣环境,使黄妈干过早失去了生育能力。黄妈干的丈夫按照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娶了黄妈学作为二房,一同生活。两个老人心地善良,勤俭持家,妹妹织布,姐姐卖布,二女侍夫,和谐生活,相依为命,直到91岁高龄的丈夫去世。
巴马县是继我国新疆之后的第五个世界长寿之乡。一个小小的长寿村,现在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八个,死亡人员的平均寿命在八十岁以上,这奇特的生命现象给了探秘者无穷的魅力。除了专家学者对高达80%的谷菜食为中心的饮食生活习惯和长寿基因的研究以外,盘阳河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了旅游者无限的羡慕和享受。据了解,每年有不少国内外老年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寿村定期居住,过侯鸟式的生活。在这里远离都市的喧闹,一切返朴归真,使人清心寡欲,达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南疆之行,来去匆匆,车窗外美丽的凤尾竹,热情火红的喇叭花,高耸入云的南国棕榈,满眼都是的峻峭山崖怪石,我们都来不及欣赏,只觉得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行......
写于2011年10月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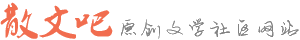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