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所记忆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把此文献给我的老班长和为国捐躯的英烈们!
哨所记忆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回忆,陪伴着我们一路走来,有幸福的,有快乐的,有悲痛的,有苦涩的,也有遗憾的。记忆深处的南疆线路维护哨所,总会使我激情满怀。
日历回溯到1984年7月。我们经过七天七夜的火车和三天三夜的汽车长途运行,来到了云南文山州平远街地区,进行三个多月的高强度临战训练。我们排提前进入战场,进行炮兵阵地测量和战场有关目标测量。任务完成后,我们担负线路维护哨所警戒任务,哨所位于老山主峰下半山腰的小坪寨点上。
当时战场环境比较复杂,经常有敌情通报小股特工利用大雨、浓雾、黑夜等恶劣天气渗入边境,偷袭、破坏我指挥所、通信维护哨、炮阵地等重要军事目标。确保这些重要目标之间以及与友邻单位之间的通信安全畅通,成了我们所有线路维护哨所的主要任务。
老山地区为热带雨林气候,地理特点:山高坡陡,沟深路少,草茂林密,毒蛇骚扰,雾大潮湿,悬崖峭壁。“山下穿短裤,山上穿棉袄”,是温差变化的真实写照。
维护哨由我们八个战士组成,山坳哨所的地理位置还算比较安全。搭帐蓬的地方,是我们用铁镐和铁锹开辟出二十来平方米的场地,四周挖好了排水的浅沟。但遇到大雨,用石头垫起来的床下就会到处流淌泥水。最头痛的还是潮湿的雾,有时早上一觉醒来,头发变得亮晶晶,被子上一摸全是湿乎乎。因此,躲进被窝里或者戴着单帽睡觉,成了大雾天夜里的一个无奈选择。军营的帐蓬不怕雨淋,就怕浓雾的渗透。当然,浓雾也有它的妙处。云雾时聚时散,有时终日不散,对于敌我双方来说都是天然的伪装帷幕。身在云雾缭绕之中,你也能享受到山外人无法享受的乐趣。当你靠近时,它就逃开,而你走了,它又尾随,与你玩起捉迷藏来。站在山巅看云海和云雾中忽隐忽现的村寨,真会令你陶醉在仙界的隐居生活之中。
人们常说:“云南十八怪,三条长虫一麻袋,二个蚊子一盘菜,黄蜂蜂窝当锅盖”。为了对付虫蛇侵袭,我们除了必备一些药物外,还经常在住处和帐蓬的周围撒些六六六粉和焚烧些当地老百姓使用的不知其名的香草。
哨所上的吃和用水是比较紧张的。连队每个星期固定给我们送一次大米、面粉、大白菜、压缩饼干等食品,几桶塑料瓶装的干净水是专供大家吃的,附近的山沟水和下雨时用七、八个脸盆积的雨水,经过明矾过滤、沉淀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 。有时,一、二个月没洗澡,也是很正常的事。炎炎夏日里,能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成了我们的奢望。有时,我们四、五个战友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冲进雷阵雨中洗澡,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一边对着群山吼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哨所的旁边,是一条直通老山主峰的小道。住在哨所或外出维护线路时,白天经常能听到弹片的呼叫声和偶尔炮弹的爆炸声;晚上睡梦中醒来时,有时也能听到从阵地上抬下来的伤残战士疼痛难忍的叫喊声;特别是深夜站岗时,看到的七、八个战士风雨中抬着伤员下坡时的艰难情景,总是不能忘怀。在哨所旁泥泞的小路上,一群全身是泥的战士为了减轻战友的疼痛、流血和保持担架的平衡,除了肩扛外,有时前面的不得不高举着手,后面的则半蹲着身,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缓慢前行。一个战士摔倒了,另一个战士顶住,相互之间还不停地喊着“小心、坚持、小心……”。
我虽然叫不出这些战士的名字,但他们风雨中的身影和这座英雄的老山一样,已牢牢地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
每次大的战斗过后,往往大部分通信线路被猛烈的炮火炸断。我们老班长严国和就是在“1.15”战斗后,在维护线路时光荣牺牲的。
85年1月17日 晚上八点多,我们接到命令,团指挥所与前线观察所的线路需要立即抢修。副班长带着我们一行五人沿着线路往山上巡查。因为晚上一片漆黑,我们打了手电筒,结果被团指挥所的参谋长发现了,十分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危。在线路试听时,命令我们按原路返回,第二天天亮再去查。
第二天刚起床,副班长就告诉我们,老班长严国和早已带着战士王立国去查线路了。没过半个多小时,我们突然接到指导员蒋申洪的电话,让我们拿着担架去老山主峰附近抢救伤员。当我们抄近道上气不接下气跑到离主峰附近二公里处时,附近工程兵部队的战友告诉我们:好象是一个班长,可能不行了,他们已用车把他送下去抢救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大家几乎要瘫软了,但我们还是坚信老班长不会离开大家。我们沿着抢修中的大路追赶汽车,一路跑到山坳里的团野战卫生所。此时,老班长已静静地躺在路边的担架上,身上盖着一床崭新的草绿色军毯,头部担架下血在汩汩地流着,渗入南疆的这片土地。卫生队苗队长静静地陪着,声音低沉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班长太累了,不要惊动他,让他好好休息吧……”。
此时,群山静悄悄,大地变沉默,天空中的雾也仿佛要凝固了,化作无言的泪珠,为老班长的英灵送行。
事后,和老班长一道执行任务的战士王立国哭泣着告诉战友:老班长和他在离海拔1422.2米的老山主峰二公里处的狭窄开阔地抢修线路时,遭到了七、八发炮弹的袭击,他们被泥土掀翻后卧倒在地上。过了几分钟,老班长叫他千万别动,自己站起来继续抢修线路。此时,又过来了几发炮弹,自己震晕过去了。当他醒来大声呼叫“班长、班长、班长”时,再也听不到老班长熟悉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老班长在战场上维护线路时矫捷的身影。
我和班长本来并不认识,我在江苏无锡当兵,而老班长却在江阴炮团。1984年的那场南疆之战,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成了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的指挥连战士。
老班长是江苏盐城人,他没有影视片中塑造的那种英俊威武的战斗英雄形象,身高1.75米左右,身体单薄瘦瘦,眉毛浓浓,鼻梁笔正,下巴尖尖,很有特色的是笑起来常会露出一点暴牙。23岁的老班长,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年轻。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许多事情已经淡忘,我也脱下军装,跨入另一条战线。但南疆那英雄的足迹,红色的土地,烽火的哨所却难以释怀,还有曾经风靡南疆的那深情悲壮的歌曲《血染的风采》的旋律,总会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荡。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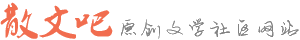

评论